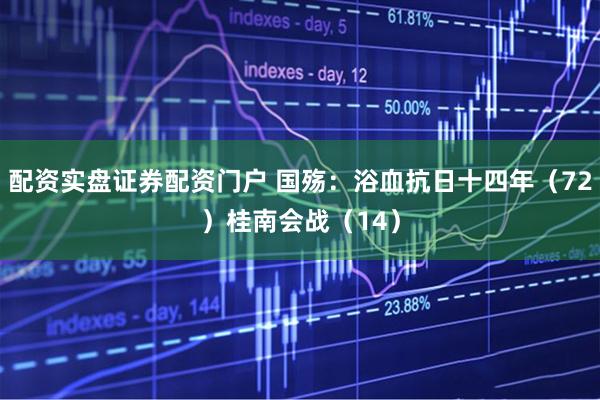
第5军攻下九塘后配资实盘证券配资门户,虽有部分归于日军第5师团主动向八塘收缩的原因,实际上是九塘、昆仑关地区近两周战斗发展的延续,也是日军在第5军连日攻势压力下,所引发的结果。
日军撤退似乎并未为中国方面所侦知,因为,第5军预想日军可能在接受了进一步新锐部队的增援后,将发动反攻,军司令部遂下令各师就429高地、441高地、石桥、六扒、六城、枯桃岭一线,尽速占领阵地、构筑工事,建立起有效之防线,以防预期中敌人的反攻。
日军坂田支队3日撤离九塘,系有计划、有准备的转进行动,不似昆仑关放弃时走得如此匆忙,于是日在离开时.尚有时间余力捧着战死者灵牌,举行召魂祭。并且,还在九塘民家墙上贴出布告,其内容如下:
“今次作战,我军昔派之九塘附近之一部,蒋军猬集攻击而来、以致发生战端,然我军乃乘此良机企图大反击至完结,其警备约经五旬,派遣于此地之我军数大队,则善能与蒋军十余师互相对峙,而继续力斗,特对该地蒋军,得以比较他方面,作出至今未见之强健奋战表示敬意。
同时,并向绝伦无比之我军之坚忍、能将优势之蒋军击退,而将威武宣扬于中外之战功,则不惜绝声称赞。
我军对此地之防守,业已到完全击碎蒋军之企图之目的,因是返还蒋军、最后对在九塘附近战死之日中两军将士之武勋,赞扬而祈其冥福。大日本军司令部。”
不明就里的中方战史作家,常引用该文告内容,指称日军实已默认其不堪再战,实则本布告的目的,根本就是在夸耀日军武功之强盛,能够以寡击众、达成任务、并“击碎蒋军之企图”。
内中,虽赞扬第5军“得以比较他方面(的中国军队)作出至今未见之强健奋战”,但仍在用以突显出日军之英勇善战,而九塘之“撤退”,则是日军主动“奉还”。
本篇布告上呈重庆后,蒋读罢后引为奇耻.并在军事会议上一字一句朗读出来。
不过,本篇布告内容、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、得以一窥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人的心态。
图片
攻占昆仑关阵地的中国军队 图片来自网络
自从七七事变中日发生战端以来,在中国大陆战场上的日军,历次会战无不以少于中国军队甚多的兵力、就能轻易击退数量优势的中国部队,赢得军事作战上的胜利,而其损失比较中国军队方面要低了许多。
在其官方文献中,动辄宣称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遗尸数、不合常理地超出日军的伤亡10倍乃至20倍以上。是以日本军官们上下一贯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、看不起中国部队,在其集体意识上已经塑造出了一种过度膨胀的心态。
12月29日,佐藤、铃木等人从南宁回到广州后,18时,第21军即向第5师团发出如下电令:
(一)军决定向南宁增调部队,歼灭集结在南宁地区的敌军。
(二)第5师团依然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,以利于新到达部队的作战。
第21军在上述电报中所提的“增调部队”,是指当时尚在广州以北翁城、英德地区,与余汉谋第12集团军进行作战的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。
中国派遣军为使广州地区在第18师团、近卫混成旅团调至南宁后,能保持相应的防御兵力,决定将在九江准备回国复员的106师团,调到广州(南宁作战结束后的2月间回国)。
而日军第21军进行的“翁英作战”,目的是策应南宁地区之进攻,扩大在广州以北的占领区。
这次行动使用了第18师团、104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分三路于12月24日(原定26日)提前两天开始。
西路由滨本喜三郎中将的第104师团,从源潭墟沿铁路攻向潖江口、连江口,于30日16时30分占领了英德;
东路由久纳诚一中将指挥的第18师团,从增城经永汉、铁岗、吕田、车埔、梅坑、回龙、青塘,于29日18时占领了翁城;
中路由樱田武少将指挥的近卫混成旅团,于从化的温泉,分两路先包围良口圩,然后攻向沙田圩,到翁城以南的太平圩停止。
日军原计划占领第四战区所在地的韶关,但中间因南宁形势吃紧,到达英德、翁城后,就匆匆结束战事。
并且,由于中国军队在翁、英地区的抵抗,作战仅一个星期,日军即被击毙239人,击伤1281人,合计死伤1520人。
随之,这三路日军于1940年1月1日即开始撤回至原出发地,准备开往南宁,第104师团在返回时,还将潖江口这带的铁路拆去一段。
在桂南,九塘的收复,标志着中国军队一个阶段任务的达成,然而,如前所述,如以桂林行营之反攻邕宁的战略目标而论,九塘、昆仑关的收复,只不过是战役初步日标的完成。
但是,以现实状况而言,中国陆军第38集团军虽收复了九塘、昆仑关,惟日军第5师团尚留有有力部队(及川支队)在八塘一线坚守,第38集团军向南宁进击之前,需先行将该股敌人歼灭或者逐退。
这其中的关键,在于各部队保有适切的兵力与战力,可惜的是,第5军因为九塘、昆仑关地区的激烈战斗,已经蒙受了相当的损失,元气大伤,其战斗力已大为下降。
从1月5日至9日,第5军继续向日军八塘前缘之防线进行攻击、进展极少,其所攻击的敌人,系新近开到战场完整的及川第9旅团第11联队,以及仍在此地台湾旅团的第1、第2联队余部,且其防务为充分设防的坚固阵地,又带有充足的给养。
图片
桂南会战中,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武器 图片来自网络
虽然,中国军队增加了第66军于左翼、第99军于第5军右翼三个军并列攻击,但攻势已成强弩之末。
有鉴于此、为了保存第5军最后实力、使其休息整补、恢复战力,以备日后再负担更重要的任务,适值由鄂西远来的第36军抵达,第38集团军遂于11日17时左右,向第5军下令:
“第5军于明(12)日7时将防务交由第36军接替,集结思陇附近,整理待命。”
第5军奉命后,于是日20时,令第200师、新编第22师准备交替,该军于九塘昆仑关一带之战斗,至此告一段落。
在日军方面,及川支队长在看到了八塘一带已经完成了防御布置与阵地构筑.情势趋于稳定后,分别于5、6两日令在九塘、昆仑关地区鏖战两周﹐业已残破的三木、坂田部队,返回南宁。
后来,第5师团今村均师团长认为,八塘守军除了第11联队系第5师团建制部队外,主力竟是友军台湾旅团的两个联队、这样的处置“对该队士气及师团之情义均为不妥”,遂取消了坂田部队调回南宁的决心。
战局停歇之际,蒋于1940年1月7日亲赴广西,与白崇禧等商讨下阶段的作战部署。
由于前一阶段蒋、白二人作战意见分歧较大,蒋认为自己的作战方针部署,根本无法通过白崇禧加以贯彻,所以,在抵达桂林后,便有了临阵换帅的想法。
在当天日记中,蒋记道:“陈诚何如?张发奎何如?抑仍由白崇禧负责乎?”
10日,蒋介石往行营迁江指挥所,听取前方战况总报告,与白崇禧在防空洞内,谈政治外交与军事诸问题,下午,与白崇禧、陈诚、张发奎、徐庭瑶、林蔚等讨论、商议作战计划及指示增调各军与前线部署。
会上,白崇禧主张趁着敌人援兵未集结之时,集中优势兵力即以第2军、第6军、第36军、第99军会同第5军发起新的攻势,一举收复南宁,与会将领也一致同意白崇禧的主张,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。
会后,蒋介石第二天返回柳州,随即反悔,主张:
“八塘战局重点,应置于六七塘之北方山地,形成侧面阵地,使敌军进退两难,并劝白崇禧不可躁急求速,更不可畏难图易,以南宁关系重要,实为全局胜败之总枢纽,不可稍有取巧与侥幸之心,必须稳扎稳打,全力以赴也。”
这样一来,原先制定的一鼓作气反攻南宁计划随即搁浅。
蒋介石在强调南宁战役重要性的同时,仍不忘敲打白崇禧“不可躁急求速”,必须“稳扎稳打”。
12日,蒋介石与陈诚、李济深等谈话,拟任陈诚兼桂林行营主任,负责指挥南宁军事,白崇禧回桂林主持全局,陈诚力辞,此方案方未实行。
随后,蒋介石飞回重庆,留下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在桂“调处人事”。回渝后,蒋介石仍急忙致电白崇禧,提醒桂南会战:
“决非轻易操急所能求成,必须以全力赴之,忍重处之,此时争速之时间已过。故不必求速。而要在求实求稳,且必本于原理原则,计出万全,则无不成功。”
对于此行的收获,蒋介石认为:
“恐难得大益,惟略识实际形势而已。”
军事上“恐难得大益”,但留下张治中与陈诚分别调处人事与协助指挥,则为战后解决白崇禧乃至桂系埋下了伏笔。
蒋介石走后,白崇禧、陈诚及林蔚等人继续会商反攻南宁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。
1月13日,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主持下,桂南地区各级战地指挥官于桂林行营迁江指挥所继续召开军事会议,研讨桂南战场尔后作战之指导与遂行。
图片
桂林行营迁江指挥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会上确定了此战的总体方针,即“以攻克南宁为目的,先确保现态势,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,对郁江两岸之敌,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”。
前往桂林行营襄助作战指挥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,以邕钦路上敌增援部队正大量运动之中,而我军部队尚未集结完毕,深恐逐次接战,徒遭消耗实力,建议三种方案:
一、着重于战略者、对邕江以北各据点如八塘、南宁等处之敌,取包围监视之势;而使用主力于邕江以南,断敌后援,相机进取南宁。
二、着重于战术者,以主力使用于邕江以北,直接强攻敌之据点,如八塘、南宁;以一部使用于邕江以南,断敌后援。
三、战术与战略并重者,于邕江南北各置重兵,合力而围歼之。
经与会将领讨论后,决定作战原则仍以攻克南宁为目标,指导要领大略与陈诚所提之第三案雷同,其内容概为:
一、方针:以攻克南宁为目的,先确保现态势,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,对郁江两岸之敌,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。
二、指导要领:郁江左(北)岸以一部兵力扼守要点,主力则向敌军之侧后方施行猛烈之攻击,郁江右(南)岸之部队,除以有力一部威胁南宁外,主力应控制于邕、钦路之两侧,以阻敌增援,相机击破北进之敌。
三、指挥:郁江南、北两岸,各设统一之指挥官,南路兵团总司令夏威;北路兵团总司令吴奇伟。
四、部队更调:第64军调邕、钦路东侧作战;第49师调桂南归还第6军建制,限一月底更调完毕。
五、第5军暂在黄墟、思陇集结补充,顶定调驻柳州。
此役,中国军队将集结了四个集团军,计15万余人的兵力。桂林行营设想沿着邕宾路、邕武路、邕钦路三路,会攻南宁。
邕宾路兵团以南宁为目标,为全部攻势之主力军;邕武路兵团为助攻,策应邕宾路兵团对南宁的进攻;邕钦路兵团则尽力截断敌人之后方交通线,阻其增援与补给品之前送。
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为:
一、在邕宾路方向,第38集团军的四个军(第2、第6、第36、第99军)与第37集团军的66军,仍对八塘之敌(第5师团及川支队、台湾联队)进行围攻,统由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指挥;
二、邕武路方向,夏威第16集团军第一纵队(第135师、第170师),对占据高峰隘、香炉岭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进行攻击。
三、在邕江南岸,日军以兵站守备队部署于邕钦路沿线上各要点、构筑有工事据点固守,并分置若干机动部队、以应付中国军队于邕钦路全线上之攻击。
中国军队在该方向部署第16集团军第二纵队(第31军第13 1师、第118师以及龙州教导总队两个团)。由公路以西,对邕钦路北段日军各据点攻击;
第26集团军第46军(第175师、新编第19师余部),由公路以东向邕钦路中段之小董、大塘等据点之敌攻击。
除以上已到战场之部队,另有八个师正在向桂南增援之运动途中,其中较重要者有第64军的两个师。所有部队可望于1月底、2月初集中完毕,于2月初开始行动。
这些部队当中,以徐庭瑶指挥的第38集团军的战力最受人瞩目﹐该集团军序列下集中了军委会调往桂南的中央直辖部队,除了第5军暂调后方整补,第2军为军事委员会直辖之战略预备队,其陆军第9师为中央直辖部队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部队。
该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,抗战前,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队整编师建军案中,第9师名列整编方案之第一期,为当时中国陆军编装最先进的调整师,其步兵团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步兵团编制编成。
此时,第9师已依1938年师编制,改为三团师,由四川出发、兼程赶到贵州都匀后,用汽车运送到广西宾阳南,接替友军昆仑关阵地。
令人感到不解的是,桂林行营于1月13日在迁江公议中,确定了反攻南宁的基本方案之后,全战区无积极与充满活力的指导,以督促各路兵团尽力进攻,且各兵团之部署亦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当时,有五个军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,新到部队亦逐次加入高峰隘、葛墟方面,各高级指挥官几无控制一兵,可作机动运用。
而邕江南岸兵力亦未能形成重点,不足以有效阻敌增援与补给,所以,在1940年春节以前.邕宾路与邕武路的攻击均无进展,而邕钦路东、西两个方向对于敌后方交通线的攻击、一个据点都没有打下来。
与其说是兵力不足或战力不如人,毋宁说是高级指挥官的决心不够,桂南战场一点都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的氛围。
实际上,由于第5师团今村师团长的一意孤行,将第5师团的主力与台湾旅团的两个联队钉死在远离南宁的八塘战线上,造成后方空虚。
假如桂林行营能够以更大的活力,更积极的态度、催促各路兵团以更活跃的姿态,仅以一部监视八塘日军,而以主力直捣日军南宁核心地区,或者确实切断钦州日军后方联络线,在日军第21军援军尚在途中的这段空当中,达成歼灭第5师团的战果并非奢望的目标。
即便歼灭的目标不易达成,至少亦可再度陷第5师团于先前第21旅团的困境,可中国军队各兵团迟缓无为,等于给了日第21军充裕的时间,使其增援转用的部队能够适时到达桂南战场。
1月14日,陈诚驰赴迁江晤白崇禧、林蔚商军事,决定今后战事将以第四战区名义指挥,张发奎仍须来此;陈诚留此,不居名义,从旁协助。
陈诚提议以粤系将领张发奎负责,乃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。
据张发奎回忆,早在一周前,蒋介石就已给张发奎发电报,指示:
“以后由余汉谋指挥西、东、北江地区的军事行动,由我(张发奎)指挥桂南的军事行动。”
但是,当时张发奎还不想赴任,因白崇禧、陈诚、李济深等人皆在广西,他无法掌握实权。如今,在“收到蒋先生的几封电报以及陈诚、白崇禧、张治中的催促后,我终于不得不去了广西”。
让第四战区真正负责指挥桂南战事,而桂林行营仅仅发挥指导作用,这是蒋介石此番来桂所做出的一大人事调整举措,也应该被看作削弱白崇禧兵权的重要一步。
反攻方针大体确定后,蒋、白出于各自利益,对反攻作战的兵力配置又起争论,白崇禧与代蒋监军的陈诚爆发了尖锐的冲突。
1月27日,陈诚奉命再次来到迁江与白崇禧会商军事,决定“由二月一日开始,并预定阴历元旦反攻”。
陈诚发现:
“我军部署,轻重倒置,行营当局,认为增援敌军,必攻我右翼,故于左翼方面未能作适当之部署,实则我右翼万山重迭,敌绝无置重于此之理。时各高级指挥官,几无控置一兵,因建议至少抽出一两个军控制机动,并应着眼左翼。”
因此,主张减少正面兵力,补左翼空虚,并分布有力部队,巩固后方城镇,但此议遭到桂系将领王泽民的极力反对。
王认为配资实盘证券配资门户,应集结重兵于右翼。而右翼主要为桂系部队,可以互相拱卫。白崇禧偏袒王泽民,陈诚的建议未被采纳,陈甚至为之“寝食不安”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华林优配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